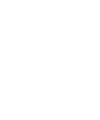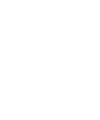谨然记 - 谨然记 第73节
“与谁结私怨都可以,犯众怒却不行。这是道,放在市井、江湖、庙堂皆准的道。”
这是那夜夏侯正南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也是夏侯正南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天明时分,夏侯正南被婢女发现死在卧房。翠植环绕里,鸟语花香中,一代枭雄神态安详,恍如酣眠。然而他确实是走了,带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恸,带着追忆往昔的伤怀,带着凶手必死的执念。这个百岁老人或许有着这个江湖上最高强的武功,最庞大的势力,最深藏的情感,却终是,敌不过岁月。
白幡蔽日,哀声震天。夏侯山庄,大丧。
乱作一团的侍卫婢女,逃的逃,散的散,十四位少侠被各自师父从牢里带了出来,摇身一变,倒成了守丧之人。闻讯而来的江湖客三教九流,有虎视眈眈的,有幸灾乐祸的,有纯凑热闹的,也有趁火打劫的,主持祭奠的圆真大师一一应对,总是护住了夏侯山庄最后的颜面。
但谁都知道,漫天纸钱里,一代武林世家,倾塌。
打下这份家业需要多少时日,春谨然不清楚,但他却清楚地看见,湮灭,只在一瞬。
七天之后,夏侯父子下葬,仁至义尽的各大派离开夏侯山庄,各自回家。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沉痛,但心里呢?
没了夏侯山庄,谁是下一个隐形霸主?杭家?青门?寒山派?
春谨然不想去思考这些,却总下意识去想。裴宵衣说人心险于山川,夏侯正南说有多少种人心,就有多少种聪明,他知道他们都是对的。可他仍不愿意这样。
从回到夏侯山庄,春谨然就没寻到与裴宵衣单独相处的机会,直到最后,他也只能远远看上一眼。那时靳梨云正抱着夏侯赋的牌位不肯放手,靳夫人气得七窍生烟,却又碍于面子不好发作,裴宵衣只得上前去夺,最后牌位夺下来了,脸上也挨了几下,激动中的靳梨云不管不顾,指甲在裴宵衣的面颊上划出浅淡血痕,隔着那么远,仍刺痛了春谨然的眼。
喧嚣散去,满目荒凉。
龙飞凤舞的山庄匾额下面,只剩孤家寡人的郭判,祈万贯,丁若水和春谨然。
纸钱的黑色灰烬被风吹起,带向空中,带向遥远,最终消失在天边。
郭判长叹一声:“什么富贵权势,都他妈黄粱一梦。”
祈万贯苦笑:“人活一世,总要有个奔头。”
郭判皱眉:“惩恶扬善,不比争权夺利强?”
祈万贯谨慎后退,躲到安全距离,然后露齿一笑:“郭大侠,道不同不相为谋。”
郭判鄙夷地瞥了他一眼:“钱篓子。”
祈万贯眉开眼笑:“借你吉言!”
郭判再不想和他说话,转身来到春谨然面前,直来直去道:“听说夏侯正南死前找过你?”
山庄人多嘴杂,这个“听说”的出处无从查起,春谨然也不愿深究,坦然相告:“是的。他怀疑夏侯赋的死不是意外,想问问我的看法。”
郭判瞪大眼睛,显然十分意外,他以为夏侯正南囚禁他们只是一时接受不了儿子死亡的现实,毕竟十四个人的供词一致,他实在想不出有何可疑:“我以为,他是想问赤玉……”
春谨然皱眉:“人都死了,谁还有心情关心秘籍财宝。”
郭判不以为然:“信不信,定尘、戈十七、房书路他们肯定已经被师父掌门亲爹盘问了七天七夜。那些老家伙,早就石头心肠了。”
若在从前,春谨然八成会附和,可现在,他却莫名生气起来。
夏侯正南最后画的那张像,被他在灵堂偷偷烧了。他不知道黄泉路上的夏侯正南能否收到,但他希望能,因为如果收到,心机深沉的老头儿一定会贴身藏好,这样即便喝了孟婆汤,转了轮回,也可以凭借画像,找到那个让他念了几十年的朋友。
一世能有多少个几十年。
夏侯正南那老流氓才不是石头心肠,那根本是个情种。
“谨然?”丁若水担忧的脸出现在眼前,“你怎么哭了?”
春谨然愣住,下意识抬手,果然在脸上摸到一把水。
“没事。”春谨然擦擦脸,深吸口气,冲丁若水咧开嘴,“咱们回家。”
第79章 桃花春府(一)
春谨然在若水小筑待没多久,便回了春府。走前千叮咛万嘱咐,若是裴宵衣来了,或者哪怕只是有一丁点消息,也要通知他。丁若水心里不爽,却还是应了。春谨然许是还没弄清楚自己对裴宵衣的感情,但丁若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过丁神医不想说破,没有原因,就是不想,谁能奈他何!
回到春府的春少侠很是胡吃闷睡了一段日子,将前些时候掉的肉都补回来了。然后,便觉出无聊来。院子里已不复往日美景,花谢叶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迎风瑟瑟发抖。春谨然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裹着斗篷,坐在院中一片叶子都不剩的桃树下,摇铃铛。
第一次见这场景时,小翠吓坏了,以为自家少爷中了邪,连忙喊来二顺。二顺走过去就是一幅字谜,少爷对答如流。可对完了,又继续瞅着铃铛发呆。那铃铛的声音很小,但听在二顺和小翠耳朵里,充满魔性。
然而除了这个怪癖,少爷并没有任何不妥,偶尔心情好了,还会亲自出去收租,依然是那个走路带风温柔和善的春府大少爷,几趟下来,租子没收多少,倒是引来了十里八村的媒婆。
这天春谨然刚打发走一个媒婆,就收到了书信。他等不及回房,当下便在寒风中拆开来,结果寄信人并非丁若水,而是祈万贯。但要说这事情呢,也同丁若水有关。简单说,就是琉璃从万贯楼跑回来了,祈万贯来寻人,丁若水不放。但个中缘由,祈万贯并未在信中详讲,只是恳求春谨然能去若水小筑一趟,帮着劝劝,当然肯定是要把人往万贯楼劝,而且还说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春谨然对于祈楼主的“重谢”实不敢抱有幻想,但日子真真太无聊,也就决定动身,去若水小筑一探究竟。
“过程就是这样,”若水小筑客房里,祈楼主眼巴巴望着“援兵”,就差几滴眼泪,气氛便能烘托到极致了,“谨然贤弟,帮哥劝和劝和吧。”
春谨然无视对方强行称兄道弟的行径,满眼鄙视:“过程就是一句话,你受不了琉璃让你当众下不来台,所以睚眦必报,直接赶人出门。后面半个多时辰的什么你有多委屈多隐忍多大度多被逼无奈都是苍白的辩解。”
祈万贯扁扁嘴,一脸可怜兮兮:“我先是被琉璃骂,后来被兄弟骂,这两天被丁若水骂,总不能到你这里还帮着你骂我自己吧,天底下哪个帮主有我惨!”
春谨然叹口气,他大概能明白祈万贯挣扎矛盾的心情。事件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一单生意上门,琉璃觉得不划算,不想接,祈万贯觉得开门迎客,不能挑肥拣瘦。若在从前,万贯楼的弟兄们肯定以祈楼主马首是瞻,可祈楼主去西南的这两个月,琉璃不知使了什么法子,竟让万贯楼的弟兄死心塌地把他当成了自己人,说是手足都不过分,于是兄弟们既不好得罪楼主,又不愿断了手足,索性围观。最后的结果,自然是祈楼主被毫无悬念的碾压了。然,作为一手建立万贯楼又掌舵其于风雨飘摇中多年屹立不倒的男人,总还是有点血性的,于是输了口舌之争的祈楼主,恼羞成怒,抬出了自己的身份,直接将琉璃逐出万贯楼。
祈万贯仍在控诉:“你是不知道,他现在楼中威望奇高,那脾气大得谁都不能惹,说话还刻薄得要命。我是一楼之主啊,当着我兄弟,一点脸面不给我留,我若不立威,以后哪个兄弟还服我管?”
春谨然想说我怎么不知道,我太知道了,我当初第一眼见到琉璃就本能地想绕开走。那小子看着干干净净,秀气可爱,小白狗似的,可你要真去摸,他绝对一口咬得你鲜血淋漓,然后你才发现,你看错了,原来那是一只白狐狸。但眼下祈楼主的控诉仿佛裹脚布,绵绵不绝,他着实不想再给友人添堵,遂拍拍对方肩膀,柔声安慰:“反正你也把人赶出来了,他以后不会在你头上作威作福了,伤心事就别再……”说到一半,春谨然停住话头,这才琢磨出不对味来,“我怎么记得你好像是来恳求他回去的?”
祈楼主闻言收敛委屈,正色起来:“嗯!”
嗯你妈个蛋啊!春谨然感觉之前耐心倾听“牢骚”的自己简直蠢到了雾栖大泽:“你既然对他一千个不满一万个讨厌,人走了不正好舒心顺意,干嘛又颠颠把人往回求!”
“因为这个!”祈万贯变戏法似的拿出个本子,目光忽然变得炽热。
春谨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是啥……”
祈万贯的语调里带上诡异的兴奋:“账本!”
春谨然黑线,大概明白了:“他给你赚了多少银子?”
“一千零三十四两八钱!两个月啊,只用了两个月!!”
“别、别激动,你口水喷到我了……”
一番促膝长谈下来,春谨然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祈楼主的“诚意”。虽然上次琉璃想加入万贯楼时,他的态度也很热情,但远没到非你不可的地步。现下,则真是幡然悔悟,负荆请罪,一片赤诚,不死不休!
暂时安抚了祈万贯,春谨然又去找丁若水。丁若水的态度很坚决,不可能。春谨然早有心理准备,若是可能,祈万贯就不会惨兮兮地给他写求救信。
“说说你的理由。”春谨然也不急,耐心地跟丁若水沟通。
丁若水一张脸气鼓鼓的,显然余怒未消:“我把人交给他照顾,他可照顾得真好,一通臭骂然后逐出家门。现在后悔了,想求人回去,门儿都没有,我绝对不会让琉璃再入火坑!”
“我看琉璃也没伤到哪儿啊。”春谨然给友人倒了杯凉茶,“来,消消火。”
丁若水有点哀怨地瞪他一眼:“都立冬了。”
春谨然扑哧乐出声来,还记得冷天不吃寒食的养生之道,说明丁神医也没有真的怒急攻心:“我不是想劝你同意琉璃回去。”
丁若水怀疑地眯起眼睛:“那你大老远跑来干嘛?”
春谨然嘿嘿一笑:“看热闹。”
这话倒也有五分真,因为春府的日子实在太无聊了,再不找些事情打发时间,他会闷死。
丁若水对友人的赖皮赖脸从来都没抵抗力,对峙半天,末了叹口气:“说吧,你到底希望我怎么做?”
春谨然敛起玩笑,认真道:“我希望你什么都不做。既不用劝他回去,也别阻拦他回去。”
丁若水嗤之以鼻:“他根本就不想回去,还用我阻拦?”
春谨然不置可否,他还没见过琉璃,不好下什么结论,但无论如何,这是琉璃自己的路,总要摒弃外部干扰,遵循自己的心才好。后悔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无论程度大小。
春谨然去找琉璃的时候,他正翘着二郎腿嗑瓜子儿,手边一盏清茶,香气袅袅。春谨然预料到不会看见一个怨妇,但也没想到这家伙活脱脱一个等着妾侍来斟茶认错的正房。
一瞬间,春谨然就理解了祈万贯,不,是同情。祈万贯真算是百里挑一的好脾气,换成裴宵衣,春谨然有些恶趣味地想,八成琉璃在呛出第一句的时候,已经皮开肉绽。还想等着人来道歉?追杀上门差不多。
“你别来劝我,谁劝都没用。”琉璃没等春谨然进门,便堵住了他的路。
春谨然饶有兴味地打量他,半晌,忽然感慨似的道:“你好像有些变了。”
琉璃怎么听都觉得这不像好话,下意识皱了眉。
春谨然从容进屋走到茶桌旁,拣他对面的凳子坐下来,不紧不慢地给自己也倒了杯茶。那茶不知什么品类,芬芳扑鼻。
琉璃不太喜欢春谨然这个样子,因为他摸不透对方的想法,对方越淡定,他越急躁,索性主动接话:“人总是会变的。”
“越变越好自然可以,”春谨然说着说着,忽然叹息,看向他的目光也闪出失望,“但你却是变得没从前可爱了,实在可惜。”
琉璃的脸色黑下来。
春谨然视若无睹,仍自顾自道:“通常来讲,这种变化会出现在环境骤然舒适之后,人不懂得收敛,不知道畏惧,自然也就不再乖巧可人。”
琉璃定定瞪着他:“说人话。”
春谨然乐意之至:“就是惯的。万贯楼的弟兄们太宠着你了,把你惯坏了。”
琉璃脸上乌云密布,却把嘴唇抿得紧紧。
春谨然用指甲盖都能想出琉璃在万贯楼的生活。试想,什么样的弟兄会在常年揭不开锅的情况下依旧对扶不上墙的楼主不离不弃,说穿了就一个字,傻。这样的人碰上琉璃这只小狐狸,也就一个下场,被耍得团团转。而且从人以群分的角度去考虑,能跟着祈楼主的傻子,脾气和心肠肯定也硬不到哪里去,面对这么一个粉雕玉琢还能搂银子的主儿,即便不供起来,定也是当亲弟弟那么爱护。时间一长,想不把人惯坏都难,更何况琉璃心性未定,还是胡乱生长的年纪,除了丁若水,没对谁低过头,也就难怪让祈万贯下不来台。
“不过换我我也宠你,”打个巴掌给个甜枣,是春谨然的一贯策略,“财神爷下凡哪,带来的都是真金白银,任性一点,脾气坏点,也值嘛。”
琉璃的脸色有所缓和,哼了一声:“就他们的脑子,能活到现在都是侥幸。我就没见过比他们还笨的人,什么吃力不讨好接什么,什么赔本干什么,就好像还嫌自己不够穷似的!”
“别生气别生气,”春谨然揉了揉少年的头,“他们穷他们的,反正你都回来了,他们就算饿死也不关你事。”
琉璃愣住,似乎对春谨然描绘的这个场面不太喜欢,秀气的眉毛蹙起,嘴唇被咬了又咬。
“不过他们也未必会饿死,”春谨然话锋一转,“世上会赚钱的人多了,没了你,他们再去找别人呗,反正都是赚钱,谁带着他们赚不一样。”
“那怎么一样,”琉璃想也不想就反驳,“我是真心想让他们腰缠万贯,别人可不一定这么想,说不定他们被卖了还替别人数钱呢!”
春谨然囧,所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呢,腰缠万贯这个词还真是满满的万贯楼风格,也不知道那些爱护他的哥哥们一天念叨多少遍这个宏愿。
琉璃意识到了自己的事态,赶紧又把嘴巴闭紧,脸色涨得通红。
虽然在赚钱方面天赋异禀,但终究还是个少年,几句话,就露了真心,春谨然又岂会不不懂:“其实你挺喜欢他们的,是吗。”
形式上的问句,陈述的语气。
琉璃垂下眼睛,好半晌,才闷闷道:“他们对我很好……”
春谨然说:“丁若水也对你很好。”
“那不一样,”琉璃其实也不太明白这其中的玄机,只能去讲模糊的感觉,“师父对我的好,让我想去尊敬他,报答他。可在万贯楼里,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我就想跟他们待在一起,很自在,很舒服。其实我最初去万贯楼,只当它是桥,一座连通若水小筑和江湖的桥,江湖那么大,我不能贸然去闯,要先在桥上看一看,可是后来,我就不想往前走了……”
春谨然的心软下去一块。琉璃自幼没了父母,在心底深处,怕是想要个家的。若水小筑可以让他遮风避雨,却总是少了几分归属,每次他来这里,总觉得这对师徒不够亲近,现下想想,许是丁若水醉心医术,琉璃又敬畏师父,久而久之,也就这般相敬如宾地过下来了。可家不该是这样的,家应该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任性就任性,想打闹就打闹,关起门来随便你在地上打滚,不用顾忌老天下雨刮风,不用顾忌外面街坊四邻。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