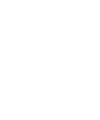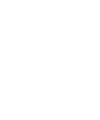上京宫情史 - 上京宫情史 第11节
王药浑不怕她,眼皮子翻了翻,慢声慢气说:“皇后见恕。臣身子不便,不能骑马。”
完颜绰被他一噎,就上次那几板子,一半的数量都是敲在地上的,揍他屁股上那几下也绝算不上重,早该好透了——她的胳膊都好了,他的屁股还没好?真是会推卸!
☆、落马
他不给面子,完颜绰自然也不给面子他。她笑道:“不就是陛下命令开导王令史几板子?听说三日后部院召见令史任新职位,王令史转天就坐在吏房的冷板凳上抄抄写写忙活了五六天,那时候能坐,这会儿不能骑马?”
王药没有被她激怒,漠然地笑笑,悠然说:“回禀皇后,臣没有说臀有杖伤不能骑马,而是臣今日晨起头目昏昏,本不能来应卯,怎奈吏房的主事非说非来不可,只能勉强陪侍陛下。但是马是绝乎骑不得的,还望皇后见谅。”
完颜绰媚然一笑,突然转了脸色,眉立喝道:“给我把他架马上去,我看他摔不摔下来!”
北院的几名武官,正想看南人的笑话,“嗷呜——”一声哄上去,抬起王药真个架到马背上去了。
王药扯着马鬃,气哼哼不言声。完颜绰学着他惯常的样子挑了挑眉,也不言声。恰好此刻响起了出猎的鼓声,行猎如布阵,讲究个行动齐整有序,大家侧耳听着鼓点,然后踩着自己的点子,策马扬鞭,向已经围好的偌大一块猎场奔去。
地面的黄土被马蹄扬起来,烟尘滚滚,别有气势。完颜绰的金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皇帝的旌旗在正前方领路,她也不甘落后,将马缰一拎,随着她的一支队伍便齐刷刷地朝着林深处而去。她经过王药身边的时候,见他还假惺惺在马背上摇摇晃晃的,不由嘟囔了一声:“叫你装!”一鞭子抽在马屁股上。
那马是训练有素的战马,吃了一痛,本能地撒开四蹄就跑。王药的双脚还没踩进镫子里,只能靠手里抓着的鬃毛保持身体的平衡。他右手去捞马缰,双腿去夹马腹,不料一个弄不清情况的契丹武将,见皇后使坏,竟也有样学样,恶作剧地又给了马屁股一鞭。
战马本来就被背上那个人的摇摇晃晃弄得心烦意燥,跑得好好地突然又吃了一鞭,顿时前蹄扬起来,怒声嘶鸣。背上的人哪里还坐得稳,整个儿朝右侧滑了下去。
“当心!”完颜绰惊得大叫起来。
好在那马还算通人性,接着又狂奔起来,马背上的人虽无即刻滑下马背之虞,却也在林间穿行的坎坷小路上东摇西晃。到了一处落叶丰厚的地方,树根被隐藏在厚厚的枯叶下,那马大概被树根绊了一下,身子一个趔趄,而王药终于没有之前的好运气,彻彻底底从马背上滚了下来,仰到在地上动弹不得。
后队本就是紧跟着,此刻因驱马在最前头的皇后完颜绰勒住了嚼子,所以也一个一个紧跟着拉住了马。树林里高树参天,阳光的斑痕从树叶稀疏的枝条间散落下来,在王药的脸上打着乱七八糟的网格阴影,一时间也看不清他受了什么伤。
完颜绰心急如焚,跳下来马来想凑近看看他的伤势,但心里还残存着警觉,仍保持着距离,急急问道:“王令史,可曾受伤?”
躺在地上的,像个死人一样,闭着眼睛,一声不吭,胸脯似乎都不在起伏。
就算是行军打仗时受伤,能救的人还是要救的。跟上来的人咋呼着叫军医,又上前看呼吸,看脉搏,纷纷攘攘又是“死了”又是“活着”吵叫成一片。
完颜绰只觉得眼睛发酸,悔不当初,可是她是皇后,这样的情绪怎么能显现在脸上?恰见鞭击马臀的那个武将还在傻呵呵摸着头往这里看,她气不打一处来,把心疼的热泪化作暴戾的举动,狠狠一鞭子就抽到那个人的脸上:“胡闹!若是行伍里,你莫名其妙的一记下去,不是要毁一支军队?!”
那人委屈地捂着脸,张口辩解道:“皇后不是也……”
完颜绰气得只能用鞭子说话,狠狠地捏着银鞭柄,左右开弓对着那武官一顿乱抽,打得他满头满脸的血,终于忍耐不住。契丹人粗豪,到底不似中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深入人心,不敢犯上作乱,逃跑总是敢的,捂着流血的脑袋飞奔离开了。
旁边人也来劝:“皇后,左不过一个南蛮子,您别气多了。”
完颜绰怒道:“既然归顺我国,又分什么南北?若要分南北,太_祖皇帝设什么南北院?对汉人一饭三吐哺又是为什么?我看,太_祖苦心孤诣,你们就当驴肝肺!我瞧着你们也该去好好向太_祖皇帝反省反省了!”
大家顿时不敢说话。完颜绰与皇帝一道上朝,替皇帝批阅奏折,完颜家族在朝里根深树大,撼动不起——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完颜绰若想像当年的完颜珮一样,以“去太_祖皇帝那里反省”为名逼着大家去死一死,也不是多难的事儿。
好在完颜绰心里有顾忌,怒火发泄了一些,又不敢太过关照王药,只能说些扣帽子的严重话,再远远地瞧挺尸在那里的王药一眼,亦只能无奈地吩咐:“尽心竭力去治!一切消息及时向我传话!”
动静闹得太大,前头哨鹿的皇帝也派人来问。完颜绰不敢怠慢,压下心中的焦虑忧思,换了副公事公办的模样,上马到前头行营亲自给萧邑澄回话:“事也不是大事,不过是摔了个南院的低微臣子。不过妾觉得既然陛下对契丹人汉人一概公平,绝无歧视,那么这件事哪怕是发生在汉人平民身上,也该秉公处理。”
冠冕堂皇的话几乎无从可驳,遑论萧邑澄又是听惯了皇后的话,还反过来劝了几句:“那是自然要秉公。听说你也动手痛打了犯事儿的人,若是没闹出人命,罚得也够了;若是真出了人命——”他犹豫了一下,柔和地说:“毕竟也不是存心杀人,又是自己的族人,罚点俸饷,赔点奠仪金银,也就算了……”
完颜绰冷静下来:护卫王药若是过当,万一遭到皇帝猜忌,扯出些往事来可不是玩笑的。她头一低,恢复了委屈柔和的模样:“自然的,刑律宽严并济才是正理。只是……只是妾也有些小小的悔意……若不是……若不是……”
萧邑澄笑着抚抚她的肩头:“也没什么悔的,你是皇后,就是打了没出息的南蛮子的坐骑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若是那人侥幸能活着,赏件猎物也就恩重如山了。”
到了未时,一上午打猎的收获颇丰,带着新鲜甜腥味的鹿皮、獐子皮、熊皮……一件件剥得干净,挂在树杈上;猎物的肉则煮汤的煮汤,烤制的烤制,虽然做得粗放,因为新鲜,味道也还不赖。
完颜绰惦记着王药,服侍着累了半天的萧邑澄午睡,然后大方落落地叫阿菩等侍女带上两块烤獐子肉,一大碗鹿肉汤和一碗烈酒,从军医那里问到了王药休息的地方,揭开那简陋的帐营帘子就直接进去了。
王药赤着上身,肩膀和背上有些轻微的擦伤,用生白布裹着。完颜绰已经仔仔细细问过军医,都道一根骨头没断,一块肌肉没拉伤,除了擦破几处皮,啥事儿都没有。唯独不知道是不是摔下马时撞坏了脑子,虽然一个包都没有,但是就是一直睡得不醒。
王药感觉到两根手指在扒他的眼皮,忍了又忍没有睁眼。然后是一声熟悉的冷哼,接着,鼻子眼儿里塞进一团毛茸茸的东西,他再也忍不住了,“阿嚏——”响亮的一声。
“还装呢?”
王药睁开眼笑道:“你熏的什么香?”
“什么香都没熏。”完颜绰说,“我看你是饿了,明明是肉香。”
王药自然不至于连熟肉香和女人的身体香味都分辨不清。只是睁眼后见帐营里还站着别人,那些轻浮的、尖锐的话还是咽下去了,干干涩涩说声:“谢皇后赏。”自己伸手要端阿菩手里的肉盘子。
阿菩“噗嗤”一笑,完颜绰也冷笑道:“他们怕你撞掉了魂儿,特特把你安置在这冰清鬼冷的破地方,个个儿躲得你老远,怕你那游魂会乱附别人的身,给人家带来灾难——你呀,果真是个灾星!”
王药不屈不挠从阿菩手里拿过肉盘子,撕开一块獐子肉大口吃起来,肉里头靠骨棒的地方还带着血丝,鲜嫩爽口得无以复加——在大晋,美食各式各样,可是偏就没有这样原滋原味,粗犷豪放的吃法!他又端来汤碗,煨得雪白的鹿肉汤里飘着粉色的鹿肉、酱色的鹿血块和碧绿的韭花儿,香喷喷地也很好吃。他咕嘟咕嘟喝了一碗,最后从床头一个简陋盘子里撕了两口干麦饼填在嘴里,笑道:“吃得舒服——他们小气,原本只给我一盘烂饼子做午饭。”
完颜绰看他毫不矫揉造作,吃得香,心里是说不出的适意,胸怀也豪放多了。把那壶酒搁在王药的地铺旁边。见那家伙馋酒的鬼样子,不觉好笑,板了脸说:“你不觉得还该对我说些什么?”
王药笑道:“我虽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常戚戚的小人。你虽然设计害我,逼着我骑马,还拿马鞭子抽我的马屁股,但我也不计较你。所以,不用说什么了,咱们一笑泯恩仇就是。”
完颜绰一把把酒壶拎开。
王药见她生气了,又笑道:“那好吧。臣,书令史王药,叩谢皇后娘娘赐食厚恩。——你爱听这个?”
她平常不爱听这个,马屁话么,都知道是假的,浪费时间。可是看他油嘴滑舌,满不在乎的样子,就像敢在郗家坦腹东床的王羲之,洒脱狂狷到可爱。她刚把酒壶放回去,便被敏捷的王药一把抢走了,对着壶嘴大大地喝了一口,那烈酒猛地到得喉头,一下子把他呛到了,咳了半天,却连呼“过瘾!”“快哉!”
“‘过瘾’什么?‘快哉’什么?”完颜绰一脸嫌弃,扭头吩咐几个小侍女去再拿些肉和酒来,只留了阿菩一个人在营帐里。
王药目光一凛,停了一会儿才说:“我第一次在这种荒蛮地方茹毛饮血,怎么不过瘾?怎么不快哉?”
完颜绰知道他有嘲讽意,更知道他永不服输的德性,淡淡笑道:“鹿血也算是吃过了,不知你如何‘茹毛’?外头倒是现成有刚剥好的皮毛……”她蓦然被他直勾勾的眼神打断了话头,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斗篷上的一圈黑色狐毛,狐毛衬着她粉白的脸,晃动着的额角的金珠、耳畔的珍珠,岿然不动的她雁翅般的长眉,闪闪发亮的眸子,无一不让他血脉偾张。
而阿菩,也看到完颜绰喉咙微微一动,胸口起伏得比平常厉害,她会看眼色,急忙道:“主子,我到帐营外头瞧瞧那些小妮子有没有来。”
完颜绰闷闷地“嗯”了一声。
☆、窥破
这样偏僻的帐营,这样危险的直视,让人额角出汗,心脏怦怦乱跳。
王药拱拱手,语气严峻:“完颜皇后,今日厚赐下臣,王药已经感恩不尽,瓜田李下的事,一之为甚,岂可再乎?”
完颜绰有些恼,冷笑道:“瓜田李下?你这会子装什么圣人?这瓜,这李,你没吃过?撇得倒干净!”
王药正色道:“此一时彼一时。皇后已经到了这样的位置,理应克制欲望,不要被拖得深陷泥淖。”
完颜绰有些恍惚也有些不甘。王药说的道理她明白,现在是她最圆满的时候:皇帝信赖,大权在握,最大的敌手也被扳倒了。压抑了那么久,对那个不爱的人强作欢喜,觍颜讨好,实在是累得很,很想勃发一次。然而她也明白,她的地位还必须依附着皇帝的恩宠,而皇帝的恩宠,自古以来就是倚靠不住的冰山!
完颜绰只觉得浑身都冷了下去,那种火烈的感觉消失了,力量感似乎也消失了。她又不那么愿意承认自己的虚弱,只能把自己的火气向王药宣泄:“如此说,我倒该谢谢你的提醒,从此别离,再无瓜葛?”
王药盯着她,良久微微一笑,拱手道:“如此最好。”他看到她眼睛里隐隐的雾光,心头大震,然后觉得自己才是沉入深不见底的泥淖的那个人,呼吸都被涌进心田里的泥浆窒住了。而对面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后也是个绝不肯显露脆弱的人,用带刺的话对他说:“是呢。早听说王却疾是个风流人,百花丛中翩翩而过,自然一切都看得开。女人如衣服,想穿就穿,想换就换。”
王药冲她稽首,说出来的话却既不切题,也不辩解,而是闷在嗓子眼儿里瓮瓮的:“王药不配。”
完颜绰扬声道:“阿菩?”
王药未曾抬头,听见几位侍女进来收拾东西的声音,听见完颜绰的软皮靴子踩着他帐营里的粗毡昂然出去的声音,帐门下端的木条撞在门框边,声音响亮,风把外头的秋日泥土的气味吹进来,帐中残余的她的气息越来越淡的,王药挪了挪身子,双腿已经发麻,挪动带来细细碎碎的痒痛。
外头篝火的“哔剥”声和契丹风俗的歌声响了起来,大约是开始享用猎物,载歌载舞了。这样的欢乐与他无关。午后吃了顿饱的,既然肚子不受罪,王药决定把病继续装下去,他在隐隐约约的欢乐歌声中闭目养神,睡虽然睡不着,但是可以撸顺很多事情,他看起来洒脱倜傥,其实自己知道,那是他应对这个无情的世界的屏障——可是事情并不会消失,比如他虽然有故国,有故园,但实际仍然无路可去。
另一张脸慢慢浮现在他眼前,她面目模糊,而举止娴雅,人人都说是难得的良配。然而伴生的,却是父亲的责打,母亲的抹泪,哥哥姐姐俗套的劝说。王药只觉得窒息得比刚才还要难受,在狼皮褥子的地铺上狠狠一个翻身,又努力去想汴京教坊里形形色_色的美人,她们手中箫笛琴笙,口中曼妙诗词,浅笑倩兮,美目如盼——可惜,一个个还是面目模糊。
外头突然传来一声销魂的呻_吟,声音极似完颜绰,已经迷迷瞪瞪的王药突然一激灵,已经沉重的眼皮子突然间用力地睁开。
“陛下!陛下!……”女人伉爽又妩媚的声音隐约可闻,时而轻笑,时而又娇呼。王药顿觉气血上涌,虽然明知道这再正常不过,却也手脚冰冷颤抖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觉得这“正常”里有点不正常的地方:完颜绰是有名有份的皇后,萧邑澄若是要临幸皇后,应当在条件适意的帝王营帐里,外头宫娥宦官打水伺候着,何必选这样偏僻的地方?
王药穿上靴子,蹑手蹑脚揭开帐门往外去。夜晚星月辉煌,一丛丛灌木树影被月光照得片片叶子都在闪光,蟋蟀金铃子在草丛里放声歌唱。穿过一座矮丘,隔着几丛灌木,在四围离得远些的地方能看见有几个执戟的侍卫背身立着,背着月光的地方两个人影在疯狂地动作着,叫声也不大避人,肆无忌惮一般。
骑在上头的是女人,亚腰葫芦似的充满着诱惑感。王药隐隐觉得这个“完颜绰”的身形比平常看起来略宽了些,胸前的两团剪影也丰伟很多。她俯身下去,“咯咯”笑了一阵,又低声说:“我可没皮没脸一切都给了你,你若还耳根子软,一味地只听我那个心狠手辣的姐姐的话,非要把我们母子迁出去,我只一辈子恨你。”
下头那位正在着急的时候,含混应道:“答应你的,自然会做的。不过你也要给我时间和契机,毕竟,出口的话要驳回,哪那么容易!”迫不及待抬头索吻。
上头的人影扭了两扭,惹得下头的一阵难以克制的闷哼,那丰伟的胸又垂了下去,上上下下蹭个不停,最后低声道:“你对她情分好深,不然,作为皇帝,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似乎是附耳说了个什么法子。萧邑澄“啊?”了一声,似乎没有同意。
那女子抽身要走,被皇帝的手一把拉住,转而转下为上,一边狠狠临幸,一边说:“你们姐妹,都是一样的性子——叫人又爱又恨,怎么好?”
下头那位被他撞得带了哭腔:“她恨我入骨,恨不得我们姐妹只存留她一个,若不是父亲保着我们姐妹,我们早连灰都不剩了。可是父亲年纪大了,我日日惶恐不安。我不过想带着儿子活下去,又不想掌权夺位,又是有多高的欲求?陛下以为懂她,哪里知道她在外头的恶名?但凡挡路的,都是她踩在脚下的垫脚石,她踩着多少骷髅爬到今天的位置,谁知道下一个是谁?……”
眼泪和话语都直白无顾忌,不是撒谎。男人停了一息,叹气道:“别说了,我尽力保你就是。”
他略一温柔,女人就强悍起来:“我还真不信你!”着手去推拒。
王药已经明白了大概,心里骇然,小心翼翼地慢慢后退,打算离开这样的是非之地。他白天找了个落叶厚实的地方假摔,虽然没有受重伤,但肩头腿侧还是擦破了大块的皮,动作远不及日常敏捷。后退时一条凸出的树根绊了一下,他便没有能完全稳住身子,重重一脚踏在一丛枯草里,声音在宁静的秋夜里分外明显。
动作着的两个人顿时分开,边急遽穿着衣物,边听见皇帝大喊:“都聋了?围住!”
分散在四围的十数个侍卫迅速地朝他聚拢来,王药瞧瞧身后,自知就算逃掉一时,他的营帐就在小丘之后不远的地方,也无力避嫌,索性乖乖被执,不心虚,或许有一线生机。
很快,他的头被按在散发着腐败气息的地上,那气味连绵不断地钻进他的鼻子,就像死亡的味道。他看不见皇帝萧邑澄,但听到他一个人的橐橐步伐向自己走过来。皇帝粗重愤怒的呼吸声,和王药粗重紧张的呼吸声彼此相闻,旋即穿着硬皮靴子的脚狠狠向他肩膀一踢,王药痛得喉头发咸,却动弹不得。
眼看沾着泥的靴子在他脸周围转了片刻,似乎在找一击毙命的位置。王药的太阳穴一鼓一涨,却尽力用最大的声音说:“陛下何必脏了自己的脚?”
靴子停了下来。“给朕砍了他!”皇帝低沉地暴喝。
抽刀声毫不犹豫地响起来,王药毫不犹豫地哈哈大笑,接着说:“陛下慎重!一步不周,贻害颇重。”
他的肩膀又挨了一脚,比刚才轻,但是正好踢在摔下马的旧伤上,王药张嘴呼痛,“咝咝——”倒抽了一会儿凉气,觉察那抽出的刀似乎没有往下砍的意思,才忍着痛说:“陛下下午才遣皇后那里赐送烤肉,若是晚上却又杀了,不知皇后细心,会不会觉得奇怪?若是追查起来,臣一身事小,不知陛下可能一切瞒得滴水不漏?”
他感到摁着自己头的那只手都松了松——在场就这几个知情的,事情有漏洞,自然他们首当其冲。而面前精致的硬皮靴子,也不安地在地上微微一动。
王药略微抬了点头,看见靴子上方凌乱的衣服正在被胡乱地整理着。好一会儿,萧邑澄的声音淡定了一点:“大半夜的,你出来干嘛?”
王药定了定神,说:“臣今日摔伤,半日都没能起身,陛下赐食之后,才有了些气力,所以……是起来如厕。没想到惊扰了陛下猎雉。”
雉鸡一般晚上视力弱,所以通常选择在晚间猎杀。他如此知趣,果然是个聪明人。萧邑澄的杀气减淡了很多,冷笑一声:“是呢,吓走了朕的雉鸡,不罚你可说不过去。”他目光一凛,冷冷说:“给朕打!”
随侍的侍卫都没有带打人的家伙什儿,抡起皮刀鞘不论上下就给王药来了一顿。萧邑澄居高临下看着他,好一会儿才抬手道:“可以了。”又对王药说:“你识趣,事情就揭过了;你不知趣,日后自然有的是弄死你的法子。今日这顿,先给你长长记性。”说完,拔腿而去。
作者有话要说: 我真是王药的后妈。。。
给大家送来迟到的中秋祝福!
☆、问询
周遭静下来,王药动动身子,到处痛得要命,火辣辣地连成一片,也不知道受了多重的伤。他又休整了一会儿,慢慢地撑着地坐起来,又慢慢撑着地站起来,身边一株小树,被他撑得东倒西歪的。
踢踢腿弹弹胳膊,倒还都能动弹,王药咬着牙,一步一挫地回到了自己住的简陋营帐,解开衣服一看,胳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瞧不见的背上挨得更重,估计更是惨不忍睹。他苦笑了一下,还不如被俘时宁死不屈,在牢房里被一顿打打死了,说不定反倒光宗耀祖成了殉国的忠臣,也省得遭这些零零碎碎的罪。
枕边还有军医先时留下的药酒,反正都是治疗跌打损伤的,管他对症不对症呢。王药倒一掌药酒,搓热了往青紫的地方一盖,顿时被热辣辣的痛激得倒抽一口凉气。伤处太多,如法炮制完,天边都出现鱼肚白了。他又痛又累,又心大不担心明日的事,栽倒在一堆皮毛被褥里胡乱睡下了。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