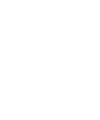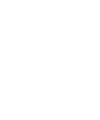古董局中局(出书版) - 第7节
“许一城是个天才,不光精通本门术业,连其他四门的门道也是一清二楚,又兼具雄材大略,深孚人望,在各界都吃得开。五脉在他的带领下,声望达到巅峰。那时节,在京沪等地,提起许一城和明眼梅花,无不翘起大拇指。买家若是一听这玩意儿被许一城鉴过,问都不问,直接包走。
“有件事你得知道,在民国之前,咱们中国人是不碰佛像的,尤其是不玩佛头。佛头这东西,只有洋人才格外有兴趣。许多国外著名的博物馆,都来中国收购,价格还都不低。古董贩子们一见有利可图,纷纷从龙门、敦煌等地盗割佛头,卖给洋人,连出了几件大案子。这些案子曝光以后,影响极坏,佛教徒和文化、考古界纷纷要求民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考古委员会呼吁,认为这是对中华文明的一大破坏。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五脉却出了一件大事。1931年,我们伟大的掌门人许一城,鬼迷心窍,跟一个叫木户有三的日本人勾结,潜入内陆。五脉中人谁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去了哪里,干了什么。等到木户有三回到日本以后,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游记,说在中国友人许一城的配合下,寻获了一件稀世珍宝‘则天明堂玉佛头’,还附了两个人的合影和那个玉佛头的照片。
“日本媒体大肆宣扬了一阵,消息传到中国以后,舆论大哗,纷纷指责许一城是汉奸。五脉也因此在藏古界声名狼藉,几乎站不住脚。你想想,谁会去信任一个盗卖文物的鉴宝人呢?何况还是盗卖给日本人。
“这件大案被媒体起了大标题《鉴古名宿自甘堕落,勾结倭寇卖我长城》,着实哄传过一阵。拜他所赐,我们五脉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五脉的家长找到许一城,要求他做出澄清或解释,他却拒绝了,什么都不肯说。民国政府很快将他逮捕,判决很快就下来了:死刑。
“许一城很快被押赴京郊某一处的刑场执行枪决。与此同时,五脉的家长也做出了决定,鉴于许一城的影响太坏,罢免他的掌门之职,同时把许家开革出去。从此五脉就变成了四脉。
“许一城的老婆倒是个有志气的女人。门里宣布开革的第二天,她就带着儿子离开了五脉,从此再无音讯。但经过这一次打击,四脉气象大不如前,后来又赶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更加衰微。一直到建国以后,在总理的关怀下,这四脉才重新改组成中华鉴古研究学会,获得新生。”
听黄克武讲完以后,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如果黄克武所说皆为实情的话,那我爷爷还真的是一个大汉奸、大卖国贼。
勾结日本人什么的且不说,盗卖则天明堂的玉佛头?那还了得?
则天明堂,那在中国建筑史上属于空前绝后的杰作。这间明堂方圆百米,高也是百米,极其华丽宏伟,在古代算得上是超大型建筑,被认为是唐代风范的极致体现——可惜建成以后没两年,就失火烧没了,不然留到现在,绝对是和故宫、乾陵、长城并称古代奇观。
武则天对明堂如此重视,里面供奉着的东西,自然也是海内少有的奇珍异宝。随便一件东西流传到现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我爷爷许一城居然盗卖明堂里的玉佛头,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看周围的人的反应,他们早就知道这个故事了——准确地说,中华鉴古研究学会的人,全知道这个故事,只有我这个许家的后裔不知道。
一想到这里,我就有点汗颜,看向黄克武的眼神也不那么有底气了。不过我心中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可又说不太清楚。
“你现在明白了?当初许家做下那等无耻之事,还牵连了其他四脉,五脉根基几乎为之不保。你若想重回五脉,就先把你爷爷的罪孽清算清楚!”黄克武训斥道,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他是亲历者,一定对许一城案发后五脉所处的窘境记忆犹新。我呆呆地看着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刘局估计是看出我的尴尬,轻轻拍了拍桌子:“黄老您别激动。许一城做错了事,那是他的问题。小许与许一城虽是爷孙,可一城死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再者说,小许的父亲自知有愧,闭关隐居,一世都不掺和五脉的事,赎罪也都赎够了。上一代的恩怨,何必牵扯到下一代、下两代去呢?咱可不能搞‘文革’那一套,老子反动儿混蛋什么的。”
黄克武冷哼一声:“照你这么说,我们就该当没事人一样,跟这个许一城的孙子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荒唐!”
刘局见黄克武说得决绝,赔笑道:“依您老的意思,小许该怎么样才能重回五脉?”黄克武略做思忖,开口说道:“若想让许家重归五脉,也简单。他爷爷不是把那个玉佛头卖出去了么?他若是能给弄回来,我黄家亲自给他抬进五脉!”
说完以后,黄克武得意地瞥了我一眼,桌子上的其他几个长辈都微皱眉头。这个条件表面看合情合理,实则是故意刁难。这改朝换代都几十年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现在让我一个小古董贩子把明堂玉佛头搞回来,那不比盗掘乾陵简单多少——且不说那玉佛头如今下落不明,就是知道下落,肯定也是价值连城,藏在什么收藏家的博物馆里。我哪来的钱买?总不能偷回来吧?
“小子,你能做到吗?”黄克武问。
我心中愤懑越发浓郁。重返五脉这事,我从来没想过,也不知道回归有什么好处。从头到尾,其实全是刘局一个人在不停地撺掇,现在倒好,黄克武一巴掌打回来,却是打在了我的脸上。
我强压住怒气,端起酒杯道:“黄老爷子,从前我不知道我爷爷和我家的来历,一直稀里糊涂过日子。今天晚上听您解惑,把这个事儿说透,给了我一个明白交代。我谢谢您,改日请您吃饭。不过五脉一事,我真没那么大兴趣。既然我爷爷是犯下了事被开革出门,我这当孙子的也不好意思厚着脸皮往里钻。玉佛头我找不回来,也不想找回来。咱们哪说哪了,今天就这样吧!”
我许家是讲尊严的,既然被人开革出门,那么也没必要硬拿热脸去贴冷屁股。
我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推开椅子要走。刘局使了个眼色,药不然赶紧起身一把拽住我,低声道:“你急什么?我爷爷和刘一鸣都挺你,沈奶奶也没说啥,三比一,黄家奈何不了你。”我摇摇头说:“我本来也没打算趟这滩浑水,你们非逼着我掺和。”药不然气得直瞪眼睛:“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进鉴古研究会,你倒好,把机会往外推!笨不笨!”
“人各有志,何必强求。”
我铁了心要走,谁也劝不住。最近这一连串事件太让人不自在了:刘局半夜约谈,药不然上门挑衅,瑞缃丰卖假佛头,五脉聚餐,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把我使唤来使唤去,从来没问问我乐意不乐意。我感觉自己成了一枚象棋子儿,人家在棋盘上想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
凭什么啊!
泥人还有个土性,耗子逼急了还咬人呢。我把药不然甩开,转身要走。刘局原本慢悠悠地啜着酒,听到我这么一说,微微一笑,淡淡说了句:“你就不想替你爷爷许一城平反?”
这一句话有如头顶“喀嚓”响过一声巨雷,把我当时就震在原地。我狐疑地转过脸去,看着刘局。桌子上的其他四位老人,也都齐齐望过去,表情各异,院子里一片寂静。
什么?平反?
平反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我爹妈在反右期间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在“文革”中双双自尽。头几年我一直忙于写申诉材料,替他们平反摘帽子。所以一听到这个词,我心里一激灵。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向刘局:“您是说,我爷爷许一城的案子,另有隐情?”
刘局从容道:“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不知道,得靠你自己好好把握机会。你往下挖,说不定能挖出些不一样的东西;你不挖,这汉奸的帽子你爷爷就得一直戴着。”
刘局不愧是领导干部,说起话来云山雾罩,从来不肯说清楚。这一席话听着七拐八绕,实则滴水不漏,什么信息都没提供,什么保证也没承诺,但却隐隐约约地抓住了我的软肋。
这个软肋,就是我们许家的名誉。我爷爷许一城若是个货真价实的汉奸,也就罢了;倘若其中藏有什么隐情,我这做孙子的绝不会坐视不理,一定会彻查到底,给他平反昭雪。我们许家人对荣辱看得极重,做人的原则也是一以贯之,对此刘局了解得很清楚,故意说出这种话来,就是想吃定我。
但我无法拒绝,无法坐视自己爷爷有平反的机会而不理——这是刘局堂堂正正的阳谋。
我回到餐桌前,双手撑住桌面,身子前倾,盯着这一干鉴古学会的老大们:“五脉我们许家回不回来,无所谓。不过许一城这件事我得问清楚。刘局,您说的好好把握机会,是什么意思?”
刘局看了眼黄克武,徐徐道:“黄老爷子刚才的故事里,已经把这个机会藏在里头了。能不能发现,就看你自己。”
我突然有一种揪着刘局衣领大吼的冲动。他到底会不会直截了当说话?每次开口总是绕来绕去的,听起来一点都不痛快。黄克武看起来也不太喜欢刘局这么说话,他的卧蚕眉一耸,开口道:“许一城当年的事确实疑点不少,但那些是些细枝末节,他勾结日本人盗卖国宝,大节有亏,可是逃不掉的。”
黄克武既然都这么说了,等于间接承认了刘局的话——刚才的故事里,确实藏有玄机。
我不顾旁人眼光,一屁股坐到诫子椅上,仔细回想黄克武刚才讲的故事,试图找出暗藏的玄机。可是要从中听到,谈何容易,我想了好久,都想不出来。好几次想开口,又都闭上了。黄克武身后那个叫黄烟烟的姑娘瞥了我一眼,眼神冷漠,说不上是嘲笑还是鄙视。
药不然倒是抓耳挠腮地想提示我什么,可他爷爷根本不让他说话。他只得拿指头敲了敲自己的头,然后赶紧把手放下。看到他的动作,我一拍大腿,猛然醒悟过来。
其实这个蹊跷之处隐藏得并不深,甚至说根本没有被刻意隐藏。我之所以之前没发现,完全是因为被我家的黑历史所震惊,顾不上去琢磨旁的事情,陷入了误区。
蹊跷之处,正是那个则天明堂里的玉佛头。
佛头在藏古界是个特定称谓,代表了两种东西。一种是念珠里的大珠,代表佛陀,还有一种,就是从佛像上盗割的佛头。
佛头这类收藏,在清末之前根本就无人问津,不算一个门类。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探险家、收藏家大量进入中国,佛像才开始被重视。不过佛像大多是石雕,体型庞大,既显眼又不易搬运。盗贼为了携带方便,都是把最具艺术价值的脑袋割下来带走,扔下无头佛身在原地。
但则天明堂的佛头,是玉佛头。除了历史价值以外,它本身的玉也很值钱。所以很少有人会去割玉佛的佛头,都是尽量一整尊弄走。藏古界有句俗话,叫“石头铁尊玉全身”,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割下玉佛头的行为,无异于是买椟还珠。
打个比方吧:如果你在路上看见一个大塑料袋里包着一叠钱,会把钱拿走把塑料袋扔了;但如果你是看见一个皮尔卡丹的钱包里放着一叠钱,你肯定是连钱包一起拿,因为这钱包本身说不定比里面的钱还贵。谁要是光拿走了钱,却把钱包扔地上,那肯定不正常。玉佛就是皮尔卡丹的钱包,玉佛头就是钱包里的钱。
根据黄克武的描述,我爷爷最大的罪行,是把玉佛头卖给日本人——这对于一个五脉掌门来说,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要是把一整尊玉佛都卖掉,岂不赚得更多?
退一步想,玉佛头卖给日本人,那么玉佛身子在哪里?则天明堂里的佛像,那一定是稀世珍宝。玉佛头现世,民国政府和藏古界一定会发了疯地去找玉佛身。可听黄克武的描述,许一城死后,这事就平息了,再没什么动静,这也不正常。
想通了这个关节,我望向刘局和黄克武,把我心中的这些疑问告诉他们。刘局听完大笑道:“你这个倔孩子,总算想明白了。”他随即又收敛起笑容:“不过你也别太乐观,这些疑问未必帮得上你的忙。”
我点点头,关于玉佛头的疑问属于常识范畴,我都能看出问题,五脉不可能看不出来。这么多年来,他们肯定也派人追查过,看黄克武的恶劣态度,就知道没什么结果。
刘局说的没错,这是个机会,但也仅仅只是个机会而已。这些疑问,有太多可能可以解释。也许历史流传下来的就只有这么一个玉佛头;也许玉佛身在战乱中被砸毁,无人知晓;或者有不知名的收藏家在机缘巧合下偷偷拿到手,从来没拿出来在市面流通。只凭着这点线索给我爷爷平反,概率实在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谢谢刘局关心,我会去设法查查。”我没有退缩。许家因为这件事,已经牺牲了整个家族,直觉告诉我,我父母的死,以及四悔斋的那块匾额,一定也与这玉佛头,和许一城有关系。我是许家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人,只有查出真相,才能给许家一个明白的交代。
我胆小,我也怕事,但这事太大了,大到我不能逃避。
看到我表了态,刘局侧身对黄克武道:“黄老爷子,您觉得这样行么?”
黄克武伸出一个指头,遥遥点着我的脑门:“看在五脉的份上,我多给你个机会。要么你证明许一城是清白的,要么你找回玉佛头。两个条件你只要完成一个,我就同意许家重回鉴古学会。”
这老爷子性烈如火,其实心思一点都不简单。看起来他大度,其实难度一点没变,反而还有所增加……
刘局环顾四周,又问药来、沈云琛,刘一鸣三位。前两位不置可否,应该是默许了。一直闭目养神的刘一鸣睁开眼睛,只说了一句:“也算公道,就依老黄的意思吧。咱们都做个见证,免得小许反悔。”
我嘿嘿一乐,这个老头子说话够毒。他明里是说我,其实是嘲讽黄克武。黄克武眉头一蹙,没说什么,倒是黄烟烟俏眼一瞪,流露出明显不满。刘一鸣地位尊崇,她不能说什么,只得轻咬了一下嘴唇。
这时刘局笑眯眯地说:“既然鉴古学会的几位理事都同意,这事就好办了。”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叠红头文件搁到桌子上。第一张是正本,还盖着大红章,底下几页都是复印件,四位理事刚好一人一张。看得出来,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东西,表情不一。
“这是一个月前外事办转给我的一封请求信,信来自东京,写信的人叫做木户加奈。她是木户有三的孙女。”
刘局这一句话,让全场都陷入一片安静。我偷偷扫视了一圈,发现无论是黄克武,还是药来、沈云琛,都露出惊疑的表情,说明他们事先也不知情,只有刘一鸣还是一脸淡然。
先是领来一个许一城的孙子,然后又突然跳出一个木户有三的孙女。我越发感觉,刘局这一次宴会,可不光是扶我进鉴古学会这么简单,似乎图谋很深,而这个图谋,与几十年前那场惊天大案息息相关。
刘局把手里的红头文件原件扬了扬,继续说道:“木户加奈在信里说,她的祖父在中国犯了侵略罪行,用不光彩的手段掠走了中国的国宝。因此她决定将则天明堂玉佛头归还给中国。现在上头正在研究,要好好搞个归还仪式,宣传中日友好……”
“啪”的一声巨响,黄克武的手猛然拍在桌面上,这一张上好的厚红枣木桌居然被拍出几道裂缝。桌子上的碗碟都跳了起来,叮当作响。
“好小子,你挖这么一个大坑,就等着我往里跳是不是!”老头的声音十分震怒。
也不怪黄克武生气。他刚做出了“拿回玉佛头,才能回五脉”的承诺,转头刘局立刻抛出这么一条归还玉佛头的爆炸性新闻,只要他多说一句“小许可以参与这个归还工作”,就算是我寻回了玉佛头,许家便可堂而皇之回归五脉——简单一句话,黄克武被坑了。
黄克武一动手,黄烟烟立刻也有了动作,她表情忽变,两道目光如闪电一般射向刘局。这时候刘一鸣身后那名男子悄无声息地往前迈了一步,恰好站在黄烟烟和刘局之间。四合院里一时间剑拔弩张。
这时候在一旁的沈云琛发话道:“我说刘局,这么大的事,你倒真忍得住,到现在才跟我们说。”她的语气里充满责怪,显然也对他的举动颇为不满。
刘局一摊手:“这事是通过外事办传达的,属于国家机密。不是我刻意瞒着几位,实在是有纪律,不到时候不能说。”
刘局和鉴古学会不一样,是正经国家干部。鉴古学会地位尊崇,可也绝不可能凌驾于政府之上。刘局抬出外事办当挡箭牌,沈云琛无话可说,只得又问道:“那这个机密现在算是解禁了?”刘局点点头,说他今天召集大家来此,正题就是说这个事。
这时黄克武一声断喝:“刘一鸣,你是早就算计好了吧!”他不再理睬刘局,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刘一鸣。看来他已经认定,刘局是冲在前头打头阵的,真正筹谋的是那个刘一鸣。
刘一鸣没吭声,又是刘局说道:“黄老爷子,您别着急。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他挥了挥手,刘一鸣身前的男子退后了两步,黄烟烟也老大不情愿地收了手。
刘局道:“玉佛头不光关系到国家文物和藏古界,还与咱们五脉大有渊源。它能归还,是件大喜事。我原来也想早点告诉几位理事,让咱们好好乐呵乐呵。可是在我们收到木户加奈的信之后,很快又接到了另外一封匿名信……”
药来奇道:“难道匿名信里说,木户加奈归还中国的那尊佛头,是假的?”
刘局苦笑道:“不错。”
在坐的人包括我顿时哑然。
刘局说到这里,表情有些忿忿不平:“最可恨的是,那封匿名信藏头藏尾,根本没说明白。现在这个归还仪式的风已经吹出去了,有好几位大领导都很有兴趣,指示一定要做好。匿名信一到,已成骑虎难下。取消归还仪式不行,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木户加奈归还的佛头是假的,更是有损国家声望。所以上头已经下了命令,无论如何,要在归还仪式之前搞清楚。”
药来问:“归还仪式定在何时?”刘局伸出一根指头:“一个月以后。”
一个月时间,这可真是有点紧。刘局对我说道:“小许,我找你出来,是希望你能够帮忙查清此事。”
我立刻明白了刘局的意思。许一城的罪名是盗卖佛头给日本人,现在这佛头却真伪难辨,其中一定隐藏着什么曲折。所以对我来说,辨明佛头真假,和查明我爷爷当年作为,其实是一件事,不怕不尽心竭力。
这一场宴会里,刘局先为许家回归五脉张目,迫使黄克武说出当年往事,引出我的决心,再抛出佛头一事,让我无法拒绝,一连串的安排可真称得上是煞费苦心——可问题来了,我虽继承了许家血脉,但鉴古的水平不见得多高,也不知道什么独门秘密,刘局费这么大力气把我扯进来,到底为的什么?
毛主席说过,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还没想明白,黄克武先不干了:“鉴定个佛头而已,有什么难的!我们黄字门的人足可以胜任,何必假手于外人?”他一指黄烟烟:“别说别人,她就比这个野小子强。”
金石本是白字门的领域,许家被驱出五脉以后,这一行当被黄字门接盘。刘局让我来鉴定佛头,等于是越俎代庖,动摇了黄字门的权威。我若是顺利完成任务,许家就可以回归五脉,对黄字门更不利。
面对质问,刘局用两个指头敲了敲桌面,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您的人真可以胜任,也就不必去偷小许的那本《素鼎录》了。”是言一出,十几道炽热的视线在小院里交错纵横,每个人都露出了不一样的表情。药不然冲着我摇摇头,表示自己真不知道。
我吓了一跳。下午我那儿才被盗,这会儿刘局就已经知道真相了?看来方震早知道实情,没告诉我而已。这些人做事,全都一个德性,吞吞吐吐藏着掖着,没一点痛快劲儿。
黄克武也没料到刘局会这么说,回头低声问了黄烟烟一句,眉头大皱,转头道:“玉佛头事关五脉,你找外人插手,理由何在?”他的调门比刚才低了不少,看来是被刘局拿住了软肋。
刘局解释道:“玉佛头这件事太敏感,如果五脉一动,藏古界的其他人也会闻到风声。到时候佛头没还回来,自己家院子闹得沸沸扬扬,上头可就被动了。小许是白字门后人,严格来说也不算外人,他平时又不混藏古界主流,由他出面最合适不过。”
说到这里,他把黄克武的酒杯扶起来,重新斟满,恭恭敬敬递过去:“您不是一直想考验一下小许么?这次玉佛头的真伪之辨,正好看看他的能力。若他把事情办砸了,别说您,我都不会让他进门。”
如果我把事情办好了会怎么样,刘局没说,也不用说,给黄克武留个台阶。
黄克武犹豫了一下:“我黄门荣辱事小,五脉佛头事大。他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我让烟烟跟着他。”然后他对自己孙女贴耳说了一句。
黄烟烟听完吩咐,走到我跟前,双手开始解衣扣。我吓了一跳,以为黄家要给我配个陪床的,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两步。黄烟烟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双手从敞开的衣襟里拿出一个挂饰,从脖子上摘下来递给我。原来人家的挂饰是藏在衣服里,解开第一个扣子是为了方便拿出来。我差点会错意了。
她递给我的这东西,是个小巧的青铜环,上头用一根红绳穿起。这枚小青铜环,表面锈迹斑斓,隐有五彩,看形制是个古物。我拿在手里,隐隐能感觉到一阵温热,不用问,肯定是人家姑娘家贴身的温度。
这玩意是古人用来束带的,不算稀罕东西。但这个上面居然嵌着金纹,走成蒲纹样式,跟绿锈相衬颇为华贵。我拿在手里一掂量,就知道不是俗物。
黄克武道:“这东西赔给你,够了么?”我听出来了,他今天被刘局摆了一道,不甘心,还要考我一考。这东西能挂在黄家子弟的身上,一定有它独特的原因。我要是看不出所以然,傻乎乎地收下了,说不定就中了他们的计。
我把青铜环捏在手里,摩挲了一阵,没有说话。药不然冲我做了个暧昧的手势,又指了指黄烟烟,意思是这东西是人家姑娘贴身带着的,刚拿出来你就摸个不停,太猥琐了。这小子,太损了。
我用指甲偷偷抠了一下青铜环上面的铜锈。古铜锈特别硬,假铜锈都是胶水做的,很软,一抠就进去。我稍一用力,指甲就顶弯了,硬得很!其实我是多此一举,这枚青铜环的真伪,不用鉴别,肯定是真的。这里全是行家,若是黄克武拿个假的出来,那是抽自己耳光。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