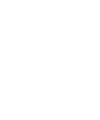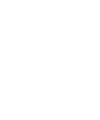情迷1942(二战德国) - 仲夏夜之梦7(赫琬平行世界番外)
过去两个月里,官邸三楼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克莱恩回家的频率从偶尔变成了几乎每晚,他的理由总是冠冕堂皇:“总部咖啡机坏了”,“某些机密文件在家里核对更方便”。老将军每次听到这些借口,都会从报纸后面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却从不拆穿。
那间原本鲜少有人问津的小图书室,也渐渐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教学场所”。
金发男人总能“恰好”在她埋头学习时出现,用他那套独特的方式指导她的德语。
女孩从最初结结巴巴的“Guten Tag”,到现在能流畅朗读《格林童话》的片段。她的进步快得让其他家教都感到惊讶。
他会“顺手”带回来一些小东西:有时是裹着漂亮糖纸的牛奶糖,说的是“总部会议发的,我不吃甜的”,有时是一个蓝色的猎豹玩偶,说是“柏林动物园发的纪念品,战友送的。”
俞琬渐渐发现,这个凶巴巴的讨厌鬼会在她夜里咳嗽时,让女仆悄无声息在门外放上一杯温蜂蜜水。
他会在她因为想家偷偷掉眼泪时,“恰好”经过她的房门口,用一贯冷硬的语气说“明天带你去吃据说还行的中餐馆,别哭了,吵”。
一种无声的默契在悄然生长。
于是,在九月六日这个雾气朦胧的清晨,当女孩终于要去冯斯通菲尔德寄宿学校报道时,克莱恩理所当然地认为,不,是确信,她需要他的护送。
晨光刚漫过官邸的窗沿,克莱恩已经在衣帽间打了三场败仗。
第一仗输给领带。深蓝太像要去参加葬礼,浅灰又像赶着去咖啡馆约会,最后他选了墨绿色暗纹款,纯粹因为上周四那瓷娃娃说“书房那幅油画的绿色真好看”
只是巧合,绿色有助缓解视力疲劳,监护人应当考虑这些。
对,监护人。
这只是替父亲履行他对朋友的承诺,善始善终,毕竟这两个月,她的德语进步有目共睹,大部分功劳在我。
第二仗输给外套。军装外套威严过头,衬衫又像要去度假,最后黑西装胜出,既能镇场子,又不至于吓坏刚睡醒的小动物。
第三仗…第三仗输给一面镜子。
镜子里的男人金发一丝不苟,湖蓝色眼睛却泄露了罕见的犹豫。赫尔曼·冯·克莱恩这辈子只在两件事上犹豫过:十八岁该选骑兵还是装甲兵,以及今天该提前几分钟下楼。
提前二十分钟刚好,三十分钟?太急切了。十分钟?如果她提前出来了。
最终,他制定了精密作战方案:七点整“恰好“把车开到主宅门口,这个“恰好”需要他六点五十就占领驾驶座。
在那之后,这位帝国最年轻的党卫军中尉,又面对三样东西,罕见地陷入了哲学思考。
瑞士莲巧克力礼盒,太普通,像敷衍。镶嵌珍珠的钢笔,太正式,像约会礼物,引人多想。柏林动物园年卡,太幼稚,像父亲哄闹脾气的小孩。
“该死。”他烦躁地揉了揉眉心,这个从前只在战术推演遇阻时才会出现的动作,最近却频繁得反常——仔细想想,就是从那瓷娃娃捧着德语课本,皱着眉问“第三格变化为什么这么难”开始的。
他索性决定三样都带,就放到副驾驶座位上,像是不小心落在那里的。她看到时应该会开心,那双小鹿眼睛亮起来的样子...还算挺顺眼。
七点整,金发男人已经坐在宝马328的驾驶座上,他特意没有让司机开车,有些场合,私人一点更好。
他计算过时间:瓷娃娃通常七点下楼吃早餐,大概会磨磨蹭蹭到七点二十出门。
可七点十分,他就拨通了官邸内线。
“让她下楼。”他对着话筒说,语气是惯常的命令式,“第一天报到,不该迟到。”
挂断电话后,他忽然又想起什么,从手套箱里取出一小瓶东西,是柏林老牌药房的晕车药水,上次去波茨坦途中,她脸色苍白地说有点头晕。
有备无患,她那种娇滴滴的体质,肯定需要。男人把药瓶放进西装内袋靠近心脏的位置,这发现让他眉头狠狠跳了一下,但最终没去调整,纯粹因为懒得动。
一切就绪。现在只需要等她出现。
七点二十,大门依旧紧闭。
克莱恩的手指开始敲击方向盘,嗒,嗒嗒,嗒。该不会又去睡觉了?五分钟后,门终于开了。
可出来的是管家:“阁下,俞小姐在找一条手帕。”
“……”
空气安静了三秒。克莱恩面无表情地点头,连手帕都能弄丢,确实需要监护人,这个结论非常合理。
他设想过所有场景:她匆匆跑出来,手里还抓着没吃完的面包;或者怯生生地站在门口,用那双小鹿般的眼睛看着他…
然后,他会用晨间德语问答巩固她的发音,驱车带她去学校,最后以监护人的身份完成入学手续——整套流程他昨晚推演了三遍。
但绝不包括眼前这一幕。
一辆挂着中国驻德使馆牌照的黑色霍希轿车,稳稳停在了官邸主宅门前。
车门打开,先踏出的是一双擦得锃亮的军靴,然后是制服,墨蓝色呢料,灰色领章,年轻军官身姿挺拔如松。
让金发男人眉头拧成川字的是,那中国军官手里拿着一个红木盒子,刺眼得像面战旗。
这人是谁?
这念头未落,克莱恩已猛打了个方向盘,油门踩实,宝马328引擎发出一声轰鸣,以一个刁钻的角度,稳稳横停在霍希正前方三米处。
而正在此刻,主宅大门终于缓缓开启。
俞琬提着个小小的皮质行李箱出现在台阶上,她小跑着过来,穿着学校的墨绿色制服裙,戴着墨绿色发卡,衬得皮肤愈发的白,一缕不听话的黑发挣脱发束,随着奔跑在颊边欢快地晃着。
“对不起对不起!”她气喘吁吁跑到车窗前,“我找不到手帕,结果发现……”到了这儿,她声音弱下去,睫毛轻颤着投下阴影来:“被海曼坐在屁股下面了。”
那只该死的蠢熊,迟早要处理。
“上车。”
他压下烦躁,冷硬的命令刚出口,就看见女孩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不是因为他,而是越过他肩膀,锁定了后方那个穿墨蓝色制服的军官。
周哥哥也在?她下意识往前迈了半步,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看了眼克莱恩凌厉的侧脸,脚步顿时变得犹豫起来。
周瀛初,国民政府驻德少校武官,也是父亲曾经最得力的副官,弗吉尼亚军校毕业,今年不过二十六岁,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哥哥的挚友,是她从小就喊着“周哥哥”的人。
记忆里的海风忽然扑面而来。
那是在来柏林的远洋邮轮欧罗巴号上,巨大的船体破开海浪,颠簸起伏。十六年来第一次离家的俞琬晕船晕得厉害,吐得小脸煞白,蜷在头等舱的沙发里,连最喜欢的奶油小饼干都吃不下一口。
父亲被同船的外交官们缠住讨论时局,只有周瀛初一直陪在她身边。
他换下了笔挺的军装,穿着简单的白衬衫,他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小罐清凉油,指尖沾了一点,涂在她太阳穴上,清冽的薄荷味瞬间就驱散了那种晕乎乎的感觉。
“阿琬,忍一忍,再过几天就到了。”他的声音总是那么平稳,裹着令人安心的力量,“你看窗外,有海豚。”
她当时迷迷糊糊地凑到舷窗边,果然看到几抹银灰色的影子跃出海面,在月光下划出流畅的弧线来,注意力全被吸过去,连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都忘记了。
“阿琬。”那一声久违的小名,把她猛地拉回现实来,他微微低头看她,眉宇间是那种克制的温柔:“将军特意叮嘱我今天一定要亲自送你入学。”
克莱恩的手指在西裤口袋里骤然收拢。
他听不懂中文,但那个单字“琬”却清晰得刺耳,不是“俞小姐”,亲昵得像在唤自家妹妹。
湖蓝色眼睛如同狙击镜里的十字准星,瞬间完成战术分析:军衔少校,比他高两级;军姿,散漫的美式作派;距离,离她不足1.1米,早已超出安全范围;表情,眼角含笑,浮夸又碍眼。
下一秒那人抬起手,动作熟稔得像是重复过千百次:“头发怎么又没梳好。”
砰!
在意识到的时候,克莱恩已跨出轿车,关门的力道比平时重了三分,防弹钢门发出的闷响,惊飞了树梢的白头翁,也吓得俞琬肩头颤了一下。
周瀛初的手将将伸到一半。
克莱恩的手帕已然递了过来,那块雪白的亚麻方巾边缘还绣着家族徽记。
“擦汗。”他的声音平稳得像在宣读军事命令,唯有喉结几不可察地滚动了一下,“你跑太快了。”
俞琬愣愣接过手帕,这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额角确实出了层细汗,她小声说了谢谢,手帕上有淡淡的雪松香,和现在笼罩着她的气息…一模一样。
周瀛初的手在半空停顿一秒,转而提起描金食盒:“趁热吃?唐人街买的酒酿圆子,你哥说,你小时候能一口气吃三碗,不给吃就哭鼻子,吃完了又撑得进了医院。”
俞琬的脸“腾”地烧了起来,一半是被戳中幼年糗事的羞窘,一半或许是克莱恩读不懂的,某些属于共同记忆的暖意。
他在说中文,故意的。
克莱恩听不懂每一个音节,但很显然,他读得懂那嘴角弧度,那是种“我认识她更久,我知道她更多”的笑容,下颌倏地绷得更紧了。
食盒揭开时腾起白雾,酒酿的甜香混着桂花蜜的气息扑面而来,圆子雪白滚圆,浮在糖水里,上面还撒着金黄的桂花,像极了南京路上那家老铺子的手艺。
记忆中的甜糯在女孩舌尖苏醒开来。
她的眼神不自觉软下来,指尖微微蜷起,想去接那碗温热的食盒。
“她吃过了。”恰在这时,克莱恩的德语生硬地插了进来,“而且太甜对牙齿不好。”
这是防止她蛀牙,监护人职责。
他目光径直落在俞琬身上,完全无视了另一人的存在:“准备好了?”
那语气太冷,冷得像是西伯利亚的寒风,吹散了甜香,也冷得俞琬莫名紧张,她手指无意识绞紧了裙角:“父亲说他安排了……”
“你父亲在中国。”克莱恩打断她,“在德国,你住在克莱恩家。”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